
老会战宋长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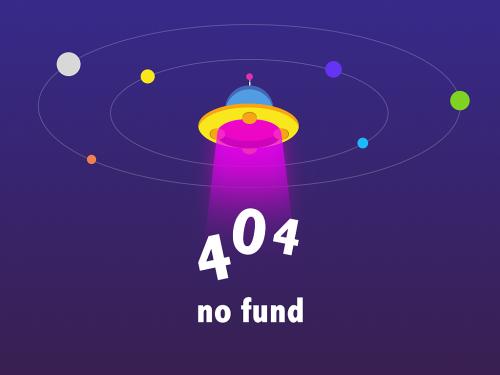
当年,“101、444”分层注水井下作业会战的老照片。
口述人:宋长新,1934年9月出生,山东省即墨人,中共党员。
人物简介:1960年3月,从济南军区某部汽车兵转业参加大庆石油会战。会战期间分别在会战指挥部运输处、井下作业处工作。
采访时间:2025年6月6日上午10时。
采访地点:创业八社区。
高龄、耳背、口音、记忆减退,是对老会战采访中最难回避的问题,采访宋老时也不例外。比如即墨这个地名,他说的山东话叫“机密”。看着我发蒙的样子,宋老不断重复这两个字,急得直叹气,最后,拿走了我手中的笔,才没再让这个难题长时间地纠结下去。
大伙儿都知道,老人耳背,咱得大声和他说话。老人呢,怕我听不清,话音也高,加上社区的屋子比较旷,我俩的对话就像在吵架,一声比一声高,常让路过的人误会地推门瞅瞅。好在宋老谦和,使用浑身解数,连比划带写,终于让这场采访顺利完成了。
农民兄弟无私相助
宋老在部队是汽车兵,来到会战一线,自然还是要干老本行。
宋老说:“从部队接到支援石油大会战的命令,到奔赴松辽大平原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我的角色也从军人转变成了工人。
“我的目的地不是萨尔图,而是安达火车站。因为我要去报到的运输处,还在安达的五道街上。
“当年安达火车站比起萨尔图算是大站。大会战在即,一些设备、物资、煤炭等源源不断地被卸在铁道线的两边,运输处当时的主要任务,就是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物资,在规定的时间内或是运往井场,或是运往露天的仓库。为了抢时间,让物资随来随走,司机不分白天黑夜,几乎吃喝甚至睡觉都在车上。
“大会战打响以后,因井下作业处缺少特种车辆的驾驶员,我先是被调去开拉油管的平板车,后又去驾驶油田作业的通井车。
“通井车是由解放车改装的,没有劲儿,载重小,样子有点像今天工程上用的滚筒水泥搅拌车。
“1960年的夏季,雨水丰润。一场场的大雨,倾泻在这片荒原沼泽上,给我们的行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那时候,像样的公路没有几条,司机驾车就在荒草和泥泞的沼泽中开行。弄不好车轮就会陷进烂泥里,越是加大油门想出来陷得越深。
“让单位来拖车,时间来不及。只能就近求助国营牧场,用他们的拖拉机帮助把车拽出来。牧场的领导对石油大会战非常支持,每次都有求必应,即便在他们最忙的时候,也没有二话,牧场的领导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:‘没啥不能没石油,没了石油,咱这拖拉机也就是个废钢铁。啥事也没有油田的事重要,先可油田的车拖……’正是他们的这种协作精神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责任感,有力地支持了油田开发初期,我们所面临的诸如拖车不足、无处居住等许多问题。”
荒草丛生井位难寻
荒原上的芦苇和杂草,时常挡住司机的视线,这使得本就无路可寻的司机师傅们,失去了方向感。
宋老说:“那时候,油田公路还没有形成网络,井场又大多在荒原深处,出车时,调度大概指个方向,我们就奔着这个方向往前开。草是一样的草,周边又没啥参照物,七拐八转就迷失方向了。
“迷路了咋办?那时萨尔图没啥高建筑,站在比草高的车厢上,一马平川,能看很远。看到有井架的地方就往那儿开,如果不是要到的井场,工人们也会告诉你怎么走能到。
“大庆油田‘五级三结合’技术座谈会后,面对‘开发三年,水淹一半’的不利局面,从1964年10月开始,会战工委作出在全油田范围内推广分层注水技术。组织井下作业职工在101口注水井上进行施工,把这些井分成444个层段,然后分层注水。当年,把这一任务称为‘101、444会战’。这一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油田开发的面貌,产油量稳步上升,意义非凡。
“当时正值三九严冬,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。井下作业喷出的水和泥浆,让他们浑身像穿了一层冰铠甲。时不时就得拿管钳敲一敲身上的冰,要不然胳膊和腿都回不了弯,走起路就像个机器人。可每个人都乐观积极,毫不退缩。战严寒、攻难关,写下了‘身穿冰激凌,风雪吹不进;干活出大汗,北风当电扇’的浪漫主义诗句。
“可能有人会想,我们这些开特种车辆的司机,往驾驶楼里一待,不会被喷得一身水、一身冰、一身泥的,是个享受的好活。你想错了,那时候,咱大庆的冬天,动不动就零下四五十度,而且我们开的是由解放车改装的作业车,功率不大,即使一直不熄火地着车作业,驾驶楼里依然热不起来,时间一长,在无遮无挡的荒原之上,坐在车里,厚厚的杠杠服,只能作为一种安慰罢了。而且,职工们干劲十足,不分白天黑夜吃住在一线上,我也怕浪费时间,一般早上带上一天的饭,就在驾驶楼里解决吃饭问题。当时,人年轻,也抗造,不管不顾地吃凉饭,常常连口热水都喝不上。当时,大家都一个样儿,也不觉得有什么苦的。”
一门三户邻里和谐
1961年之后,会战工委开始允许接家属来到油田。可当时油田还处在困难时期,职工和家属吃不饱肚子,住房也不足。面对这些实际问题,会战工委号召来油田的家属参加集体农副业生产劳动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组织起来的家属,开荒种地、盖干打垒、饲养猪牛羊、建设作坊等,不仅创造了自己的吃住条件,有了经济收入,同时也为会战职工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,为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宋老说:“我在参军前,就已经结婚。家属当时想跟着我来,但是当时油田的吃住条件都比较差,所以,直到1963年,我才把爱人从老家接到了大庆。刚来时,爱人落不下户口,油田只给了个临时户口。那时,家属是要被动员去管理站参加生产劳动的,因为劳动才有粮食补助。我当时的粮食定量是40斤,爱人的定量是28斤。
“当时,菜少,各家吃的基本上是主食。对这些定量,我们基本能达到八分饱。有人讲,吃不饱就去采些野菜。我和爱人都有自己的工作,根本没那个时间,吃饱吃不饱,也只能如此了。
“后来,有了孩子,组织上分给我一间干打垒,就是一个门里住三家的那种,一个炉烘三家用。别看那时候大家物质都不太丰富,吃的都是苞米粮子、高粱米的粗粮,白面和大米的供应是极少的,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照应亲如一家。
“到了做饭时间,虽然每家都没有啥好吃的,但大家都相互谦让着做饭的次序,因为在那个半饥饿的年代,谁先吃上一口,就能暂时解一时之饿。”
60多年过去了,当年笔直腰身、意气风发的小宋,如今已成了后背微驼、行动迟缓的宋老,但在他的内心深处,在他充满激情的眼神里,那场大会战的人生经历永远难以抹去。
红色传承
老会战是最值得尊敬的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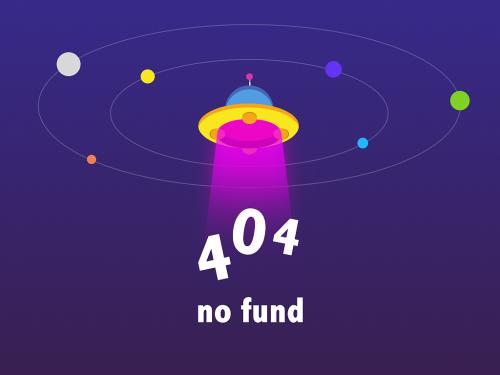
讲述人:伏虎
看着宋老弯曲的腰身,看着他额头、脸颊上布满的皱纹,看着他步履蹒跚的样子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他虽然只是那场声势浩大、举世闻名的石油大会战中普通一员,但他们那辈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,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平凡而又伟大的贡献。
在油田开发最困难的时刻,他们没有打自己的小算盘,没有把曾经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炫耀的资本,守望油田,爱岗敬业,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把大庆精神(铁人精神)的精髓呈现在我们后辈的面前,让我们学有榜样,干有标杆,他们才是大庆最值得尊敬的人。
记者:伏虎